李安三部曲又叫做父亲三部曲,因为他的的确确塑造了鲜明的中国老父亲形象——严肃,端庄,沉默,权威等等。毫无疑问的,整个电影着笔最多的就是父亲,片中所呈现的父亲形象令人津津乐道。无论是《推手》里古板严肃,处处讲究中庸之道的朱爸,还是《喜宴》中兼顾军人的严谨和父亲的慈爱的老高,亦或是《饮食男女》中表面严肃实际最先冲破伦理桎梏和小一辈锦荣结婚的老朱,都是十分立体而鲜明的。在《推手》中更是不惜用十五分钟的无对白长镜头,只为表现朱爸的生活习惯。简直是把父亲这两个字大写在镜头前,生怕观众注意不到影片中的父亲形象。
因而主流观点认为,这三部的核心都是父亲,电影的主基调是整个家庭围绕着父亲所做出的种种变化,从崇拜(或畏惧)父亲,到抛弃父亲,再到感到空虚而寻回父亲如此演绎。父亲成了整个故事的核心,成了推动剧情的关键,故事是因为父亲的一厢情愿产生的,又因为父亲的种种举措而走向高潮(《饮食男女》这一点不太明显,在另外两部是非常典型的),最终统一落脚在父亲的退场上。能够看到父亲最初所坚守的,所不顾一切而捍卫的坚定愿望最终都没有如愿以偿,而是让步,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遗憾,是无可奈何的妥协,是在寂寞中忍受,在寂寞中逐渐走向人生的尽头。所以三部曲给我的感受总归是带着凄凉色彩的,而且父亲所象征的那些文化符号,无一例外是被冲击的一方,是被残酷的现实所肢解的一方。而这些深刻的主题,肯定是要从父亲这个体角色切入,展现出他的言行,他的落寞和顽固,让观众看着父亲的长镜头特写,品味其中的主题。
李安三部曲被叫做父亲三部曲确实有它的道理。经过以上的分析,从描写的篇幅,推动剧情,表现的主题上看,父亲确实是一个无可撼动的核心角色。可是在实际观看体验中,父亲所展现出的严肃的一面并没有带给我过多的触动,可能是我见过的父亲描写太多了吧,这种严肃板正,沉默寡言,代表着中华传统的形象在我看来真的称不上新奇。甚至可以说有些老套了,毕竟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文学形象,一个经典的文化符号,有些脸谱化的成分在里面的。既然口头报告是分析父亲,按照主流的分析肯定大差不差。不过我总觉得把一切成功归结于“父亲塑造的好”这一条上,有些单薄和牵强附会了。父亲三部曲的魅力肯定不止于父亲,甚至可以大胆地说,父亲三部曲的魅力在父亲之外。在司空见惯的形象之外,还有重要的角色亟待发掘。
在搜集资料中,我发现李安导演曾在《十年一觉电影梦》这本自传写到:“拍《推手》前,我简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时银行存折里只剩下四十三块美金,这时候小儿子石头刚出生。”我猛地一惊,有一种“一切都说得通了”的醍醐灌顶之感。《推手》里艰难调和妻子和父亲矛盾,拼命挣钱打工的朱晓生。想必这里是有李安本人的情绪蕴含其中的。回顾李安的生平,他是一个兼具东方温文尔雅和西方洒脱不羁风格的导演,在他的作品中总能看到两种文化的交锋,新旧的冲突,东西的冲突;而交锋的纽带,并不在父亲,而是儿子这一个形象。如果李安在自己的作品中选择以“儿子”这一个角色来作为自己写照的话,那么想必是能够在他的作品中看到更多有趣的象征。顺着这个线索,我开始关注并思考起电影中儿子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越是深挖,越是感到奥妙无穷。
有父亲的地方一定有儿子,儿子是父亲的镜子。首先,儿子作为父亲的直系血亲,除了继承了父亲的容貌,身材等外在特征,也会继承父亲的性格特征。这一点有很好的证明:《推手》中朱晓生遭遇来自父亲和玛莎双方的抱怨,第一时间没有选择给出一个确切的答复,而是努力调停两边的矛盾。既劝玛莎多换位思考包容父亲,却也在不断的给父亲找新的去处乃至后续考虑撮合陈太,把他安置出去;没有选择借用玛莎母亲的钱买房搬家这种较为激进的办法,而是选择保持现状、努力调停矛盾;在教育杰米说他比爷爷妈妈都会照顾爸爸,指桑骂槐式地宣泄自己的不满。可以看出朱晓生的身上仍然带着父亲中式的中庸之道,在矛盾面前,采取推手的思想,不正面面对,而是想办法规避矛盾,用间接的方式化解矛盾。《饮食男女》中扮演“儿子”形象的是朱家珍,她其实默认了自己在家庭中应该扮演母亲的角色,所以即便是面对真爱也不敢大大方方地去表现自己,而且对自己这点小心思表现的异常敏感,容不得半点非议,生怕别人发现自己“大逆不道”的想法。活在自我挣扎,自我内耗的沉默苦旅中。这其实非常像其父老朱,为了维系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不断压抑自己本身的想法,和锦荣的关系只能保持在私下往来的地步,不能公之于众。《喜宴》给出的暗示更加明显了。抛开老高和伟同性取向可能一致,都为同性恋这一点外,还是能发现许多其他的相似点。比如伟同总是严肃的,他面对尖锐的矛盾,尤其是威威怀孕后,总是试图把事情包揽在自己身上,极力克制自己的情感而刻意回避与父亲可能的沟通。这和老高的做法如出一辙,他即便知道了伟同所面临的窘境,也没有做出积极的正面上的协调,而是试图通过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默默干预事件的走向。且不论两人做法的正确性,至少这种父子间不言说的沉默和自省,达成了惊人的一致。
不过如果儿子形象的存在只是为了作为体现父亲的工具,就显得太过平庸了,事实上儿子的最大价值在于破坏他本应有的形象。换句话说,在整部电影中,儿子形象就是用来解构的。契诃夫说过:“如果在第一幕里边出现一把枪的话,那么在第三幕枪一定要响。”,同样的,李安导演的电影中如果出现了像父亲的儿子,那么他一定要变得不像父亲。而且我认为这才是影片的关键所在。我发现三部曲中“儿子”的初衷无一例外的都落空了,《推手》里想要和父亲同居的朱晓生最后把父亲安置在了公寓,《饮食男女》里想要照顾父亲一辈子的朱家珍最后还是组建自己的新家庭离开了父亲,《喜宴》里想要借助假结婚蒙混过关的伟同,不仅假结婚闹出了真孩子,而且还让父亲识破了这场闹剧。而且这些并非是为了戏剧效果而刻意制造的“偶然性”事件,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些事与愿违的遗憾中,大都蕴含着必然性,正是这种必然性,揭示了中西文化差异,传统伦理道德和自由婚恋观点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性质,只是李安导演选择把这些积蓄在地底的炽热的岩浆,集中在“儿子”这个火山口喷发出来了。所以我们才会感觉这些事情似乎有着“冥冥之中必有天意”之感。可以用反向思维去思考,假设《推手》里朱晓生强行把陈太和朱爸凑一对,那他俩必然会反抗甚至闹出“假恋爱”的剧本,如果强行把朱爸安置在家中而不顾玛莎的感受,那朱晓生的家庭迟早要在玛莎的崩溃或者朱爸的崩溃中崩溃。同样的,《饮食男女》里的朱家珍是无法忘掉自己的恋人的,即便她继续陪在父亲身边,她的内心挣扎只会与日俱增直至更大更彻底的崩溃。《喜宴》里儿子如果服从了父亲,抛弃了爱人赛门选择和威威结婚,那最后他必将像他父亲那样,留下终生无法抹平的伤疤。可以看到之所以儿子没有走上父亲的老路,是因为他们敢于反抗固有的传统,敢于直视内心的渴望,敢于挑战权威和礼教。他们尊重父亲,深爱父亲,却不会屈从于父亲。正是完成了从父亲形象的圈子迈向截然相反的对立面,儿子的形象才完成的华丽的升华。这一步是影片想要传递的反抗精神,而这种反抗也被诠释成随着时代更迭和两股文化冲击下的必然现象。由此,儿子的形象完成了解构。
但我仍不满足于此,倘若真的是儿子叛逆父亲,迎接自己的崭新人生,这更像是西方电影所阐述的观点。要真如此,最终《喜宴》的大结局应该是伟同彻底和威威告别,不再考虑所谓的香火延续问题,在认清自己真爱是赛门后远走高飞,隐匿海外。《推手》的结尾也应该改为,儿子朱晓生含泪把父亲送回中国的养老院,最后一幕是对着父亲打太极的照片流眼泪。这么看《饮食男女》做的措施反而是这样的,大女儿朱家珍真的组建自己家庭去了,但是其实“儿子”这一形象却落到本渴望自由的二女儿朱家倩身上了。从这个角度看,《饮食男女》正是展示了上述两种不同的抉择,“儿子”形象在朱家珍和朱家倩手里完成了交接。一个是解构,另一个则是重建。
所以,“儿子”形象还背负着另外一个使命,重建。重建秩序,重建感情,重建关系。重建意味着破镜重圆,意味着找到新的平衡点。面对巨大的变数,“儿子”确实完成了解构的任务,但随即他们又不愿意彻底与过去告别,不愿意和父亲切割出分明的界限,毕竟这无异于剥离骨肉,斩断血脉,在父亲尚且在人世间的情况下给他宣判社会意义上的死刑。所以我们会看到“儿子”是矛盾的,他的矛盾不仅在于父亲的批判继承和延续,还在于他做出不破不立的决心后仍带着两全其美的侥幸。这种解构而后重建的抉择不会是最好的,因为破镜不可能重圆,一切回不到从前,但是却是最真实的,或者说更贴近我们中国人的。它表现为儿子在反抗后的反思,在迷惘中寻求依赖,在挣脱后又主动回归的心理。《推手》里朱晓生是怎么做的呢?他明确提出买了新房子可以接父亲,最后还是顺从了父亲的意愿给他找了间公寓住。那个曾经对父亲饱含深情和尊重的儿子又回来了,这一次是父亲率先做出了妥协的要求,儿子服从父亲的妥协的意愿,给了老朱所希望的“父子关系中最舒服的距离”,体现了推手的主题。但我认为这同样是后两部在重建儿子形象这一环节中所希望表现的主题。《喜宴》中儿子伟同的处理同样是搁置了问题,但这个问题却比《推手》严重的多,因为他终将面对抚养孩子,和两个不同性别的爱人同居诸多问题,而他所做出的妥协只是对他父亲视角下的“最优解”。《饮食男女》虽然家倩马上搬去阿姆斯特丹,而老朱也要和锦荣在新房子开启新生活,这个家不再有昔日的热闹,但是在这最后一刻老朱却品味出了家的温情。此刻一家人仍然是妥协,不过这一次选择的是抛弃家庭的自我,拥抱“饮食男女”的本我。
由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这三部电影的侧重还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把“儿子”否定“父亲”定义为解构的话,那么儿子在《饮食男女》表现的更多是解构的一面,《推手》表现的更多是重建的一面,在《喜宴》则二者兼有。这很符合我个人对三部影片的观感。要我说《饮食男女》结尾看似凄凉,原来围桌聚餐的一家人变成一父一女,实则是暗示着一家人终于从家庭束缚中解放,《推手》结尾看似朱爸和陈太没有相爱,也没和儿子同住,实则是保持了恰当的距离,给未来留下了回旋的余地。这两部是无疑的快乐结局。反而是《喜宴》结局留下了无可挽救的后果。选择留下威威和她的孩子顺应了父亲的想法,选择留下赛门则是儿子的想法。而当这两者同时出现,就不会是让伟同心安的想法。这个结局只能说是对于朱爸最好的交代。
儿子,既是孝子,又是逆子。不过还有一句话,先是逆子,后是孝子。他们也有自己的挣扎和迷惘,他们找不到倾诉的对象,只能把两代的矛盾积压在自己身上。所以他们本身就是在动态平衡变化的,犹如拴在弹簧上的球,当他们极力摆脱原点走出很远以后,却发现回归的向心力愈发强烈,当他们回到原点又无法停留。于是在逃离和回归中反反复复,在顺从和反抗中飘忽不定,儿子就是这样特殊的一代人。他们是直面整个时代变革的第一代人,是在两个世界的边界线上踽踽独行的第一代人。
假如说父亲被理解为旧时代的最后一批人,他们在激烈的交锋面前选择了妥协和退让,那么儿子就是这新旧交接线上的人。在儿子身上你能看到移民文化的端倪——所谓祖先,就是第一批背井离乡的人。这是儿子所额外继承的符号,他们是可以选择妥协,却不能安逸于妥协中的一类人。我想,从这个角度看去,三部曲中的儿子是被泛化的,是可以引起广泛共鸣的,无论这样一批人如何挣扎,又如何渴望回到过去,无论他们做出怎样纠结的抉择,或是逃避、或是让步,他们都必将无法回头,矛盾和问题无法在他们未来漫长的人生中被一直搁置下去,新旧更迭的痛苦,会属于过父子,但终将归于儿子。倘若跳脱出来看,看看我们的人生,就会发现我们的世界没有发生太多的变换,哪会有那么多悲欢离合的人生大事呢?哪会有如此戏剧性的反转再反转呢?匆匆变化的不过是自己罢了。
看着父亲和儿子荧幕里几番交锋,父亲黯淡地退让,默默的离场,儿子纠结的徘徊,或怅然或迷茫地在片尾迈出前行的一步,这些令我回想起自己。电影落幕,他们各自的人生我无从知晓,而我的人生却不知所踪。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儿子”的解构和重建,没想到终究感慨的对象是自己啊,但我身上可没影片如此好看的冲突,无非是因为家庭的期望选择了并不想要的专业,稀里糊涂地上了一年多的大学,才发现自己没有回头重新喜欢文学的路径可走。父亲希望我去从政从教,不过我从来没有这些想法,甚至填报志愿与他吵架。结局是他妥协,顺从我的想法,我当时不敢妄自为了自己的爱好而选择毫无就业前景的文学,而是选择相对好就业的专业,因为我明白自己的家庭残破的经济状况难以容许我继续我虚无缥缈的文学梦的。如今这份小小的心思,不过是停留在网上总阅读量为两位数的小说和一些文学通识课罢了,我还能做什么呢?这或许是我最大努力的在解构之后的重建了吧。我在探寻一个两全其美的答案,希望能够不辜负自己同时不辜负父亲,不过如今看来这样的抉择既不是父亲所希望的那个答案,也不是我所坚持的那个答案。我在两端反复,每每谈及此事,便会感到无言以复。不过我顽固地坚持着,即便是被现实所阻挠,那些尘封在心底的文字迟早会复活的,那些无法企及的影子,那些遗憾或者辉煌,终会一一复活的。我相信,那一张张由我印在文字里的时空会被注入新的生命,逝去的从未逝去,远去的只是自己罢了。
写完这段话时,我在家中,窗外的景色和我高中所见没有差异。似曾相识的景色宛如隐约暗示我仍在过去的岁月,我还有机会重新见识新的人生可能性。但是我明白,解构也好,重建也好,都带有“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必然性,即便是带着这些想法回到了过去,我还是会做出相同的决定。
我无法彻底地割舍父亲的期望,也无法真正的去按照他定下的轨迹活成一个木偶,我是注定要辛苦这一遭的。等到家中经济不那么窘迫,我的孩子说不定能够成为第一个触碰新世界的人,不再被传统的升官发财道路所桎梏,不再怀着幻梦又被生活压得郁郁不得志,而是活出没有我的期许的样子。
所以,我会羡慕朱家珍,认清自己想要之后大胆离去;我会认可朱晓生,明白父亲想要之后果断妥协;但我没有幸运的成为这两者。偏偏是我不觉得正确的伟同,成了我最生动的写照。李安三部曲带给我的不止于一次观影体验上的饕餮盛宴,还在于给了我一面镜子。正好借助这次报告的机会,我得以审视片中的人,审视我自己。
要是许多年过去,我大抵是记不得里面人物的名字,甚至记不清演了什么,但我绝不会忘记在一个大二的秋冬学期,我透过李安三部曲这面窄窄的镜子,和着镜中曾经痛苦挣扎的自己握手言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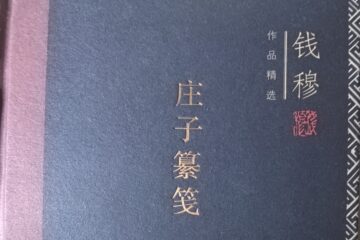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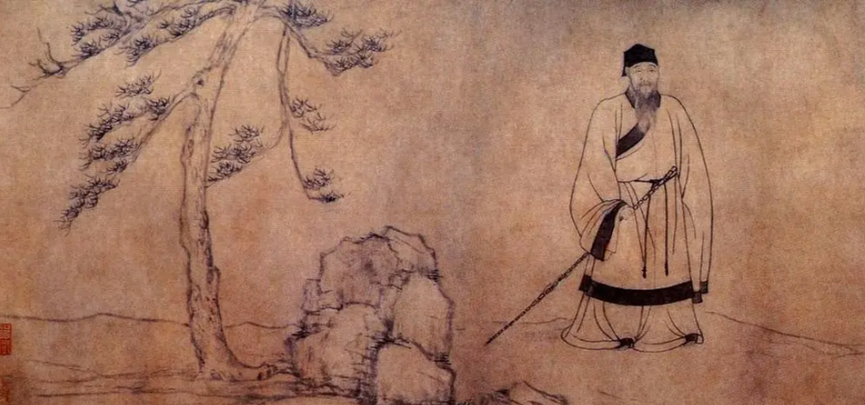
0 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