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庄子》内七篇,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庄子总以一些“奇特之人”起篇。《逍遥游》中直上九万里的鲲鹏,《齐物论》中答焉似丧其耦的南郭子綦,《德充符》中从者甚众的兀者王骀。这些人的奇特之下,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至德者或闻道者,都得到了或曾经得到真知。《大宗师》说得更加清楚:“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也解释了《庄子》在探讨真知之时,为何常常以真人起篇,并且花大量笔墨描摹真人的形貌与作为。所谓“真人而后有真知”,并没有意识决定存在的意思。相反,“真君者,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真君者,也就是真知。然而真知无情无形,可得而不可见,因此对于不得真知的芒昧众生而言,至德者至少是他们可以见到的。然后众人或者跟从至德者而闻道,或者无法用自行领悟的方式闻道,故而去受有言之教。因此,可以说至德者是真知有形的表现形式。有形不能作用于无形,但有形可以作用于有形,因此至德者的表现与世界万物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以为人们所见。
《庄子》中描述的至德者,有一些显著的、与众人不同的特点。一是无所待,不用依凭他物,可以乘御天地之正以游世间,有着根本性的主动。二是旁礴天下以之为一,窅然丧其天下,更丧其耦,也就是坐忘。物我两忘,这样在至德者的心中,本来相对待的物与我,乃至分明不同的天下万物就显现出它们的同一性。三是和通是非,休乎天钧。圣人超越是非之辩,达到物与我各自成就的境界。四是立不教、坐不议,而其众从者能有所悟得。如果从这一结果上来说至德者有所教的话,那么他们行的就是无言之教。并不是说至德者以身作则、有意施教,因为前面提到至德者的一个特点就是超越是非,而一旦对人有是非准则的教训,则又在是非之内。至德者的教,是因为其止能止众止,众人从至德者处领悟道理,就好像人对着止水自照其身,而止水本身不动。五是不以物为事,托不得已以养中。至德者不会有意教化众人,也同样不会有所偏好而主动务于任何世事,但身处人间,天行有命,即使至德者也有不得已之事,而在顺应天命而行不得已之事的时候,至德者所能做到的极致就是缘守中道,养生尽年。六是过而弗悔,不为万物所动。至德者在面对不得已而行动之时,虽表现出好恶,但心中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视万物如一。
在至德者之后,要讨论的是他们所掌握的真知。而在探讨真知之前,首先要证明真知的客观存在。就像在梦中不知道是梦,梦醒方觉梦中一切的虚假,然而醒了又真是醒了吗?如何证明醒着的当下不是另一层梦境呢?果真存在真正的醒觉吗?庄子巧妙地利用所不知的东西,解答了这个难以证明的问题。庄周梦蝶,蝶不知周。这一不知,推出物与我境域的隔断,“则必有分矣”。而不知谁梦谁,这一证明上的不知,则推出物我的相互转化、相互联系。正如“类与不类,相与为类”的道理一样,第二个不知之知命题的基础,即物我能够相互转化这一事实,正说明有分的彼此存在同一性,否则物我不可能相互转化、相互联系。而这个使得彼此的相互联系成为可能的同一性,就是客境,也就是根源性的“彼”。若没有客境,则如同风止而众窍虚,彼与此之间不能互化、失去联系,那么彼此之间的分别也就不再彰显,因此可以说客境就是根源性的主宰,或可称为真知。客境的客观性则表现在前述的第一个不知之知,也就是境域的分隔。物我不能相知,也就不能相主宰掌控,想要彼此改变就要花费努力,这就是“不得已”。有时我们对改变他物需要的努力是可以了解的,然而最根本最强大的客观性是不测的偶然,我们无法了解和控制这种偶然,这不测的偶然,也就是庄子哲学中“命”的概念。即便是真知的载体,也就是至德者,也不能完全主宰“命”作用下的“彼”与“我”。这种不可主宰性实际上正是主宰必不可少的环节,因为一者对另一者的完全主宰,意味着二者实际上为一者,无法分割,主宰关系也就随之瓦解。正因为二者有分,因此有主客体之别,因此存在着客观性。也就是基于这个道理,命证明了真知是彼与此之外的独体,与彼与此有分别。
庄子的哲学中着重探讨了用与真知的关系。不通之用是对真知的遮蔽。鲲鹏为何要直上九万里而不翱翔蓬蒿之间?正是为了摆脱遮蔽,超越不通之用,达到真知。这个比喻中暗含的意思在《齐物论》篇得到了更详细的论述。真知,也可称为道,“隐于小成而有真伪”。只有达到通之用,才能达到道通为一的境界。不通之用,就是只看到用具在实用上的功能,没有看到用具与其他世间万物的真实存在的联系。如此,就会肯定所看到的实用的方面,而否定与用具联系着的其他万物,这就是“是非之彰”。是非彰显即是小成,仅成就了不通之用,而于通之道有亏损,不能大成,这就是不通之用对真知的遮蔽。而实际上,彼与是相互转化,互为对方成就的条件,就好像“日夜相代乎前”,不能简单地肯定一方而否定、忽视另一方,而是要认识到彼与是的同一性,就好像日与夜共同的“其所萌”,此无形者不可见而可得于心,这就是通之用。圣人见通之用,因此“不用而寓诸庸”。这并非是说无所作为、不利用任何器具。庸,是一种得当而通万物的用。所谓“寓诸庸”,就是使器具得到最恰当用处的做事方法。另一方面,庄子常常提到的大而无用的比喻,是在探讨人的无用之用。这一点与器具之用又有所不同。人之用,的确仍然像器具一样,也是为他人所用。但人要达到自身的用处,不免使用器具而有所用。而当人不为所用的时候,人也就无所用,故而超越世界之外,此大也。因此,从人的角度来说,大而无用,实际上是因为无用而大。而因其超越万物,能够不受遮蔽,故而能得通之用而达到真知。
庄子在探讨真知本质的过程中,将万物的同一性、即一个根源性的“彼”作为这一本质的概念。庄子深刻地看到变化的无处不在,造化者在他的笔下拥有最强大的无力之力,甚至能负藏物以遁走。然而庄子更看到世间变化的同一性,变化本身是不会改变的绝对者,故变化本身“不得所遁”。而从那个根源性的“彼”的概念来说,真知即为真宰,其使万物成为自己,故即使是最为自觉的人,其主动性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被动的。真知,是种种变化“所由以生者”,没有这个根源性的彼就没有相对待的彼和此。真知在至德者头脑中形成的认识,乃是知化之知,其实也就是达到通之用的境界,认识到“指之非指”,即在“此”当中蕴含的与之相通相化的彼,因而没有什么是不然、不可的。根源性的彼的概念同样出现在庄子对天人的思考中。庄子以天道为根本之一,以人道为相对待的万物的不一。而人道中蕴含天道,天道产生人道,所以庄子说“天人不相胜”,天道与人道任何一方不可能消灭另一方,二者不可分割,恒常共存。
得真知者,可以超越世间无息止的是非之辩。从这个角度讲,真知即“是与非相依凭”这一道理所在,也即圣人和通是非,能以彼之非为是,而以彼之是为非的“明”。然而圣人不由是非之道,而以此明照之于天,使根源性的“彼”能够彰显。庄子在解释真知何以能够和是非的时候,给出了其为道枢的概念,实际上与之前探讨的一样,也是指彼与是的同一性,使得彼与是失其耦对。庄子又言道枢得于环中,在我看来,这概念与莫比乌斯环的特点不谋而合,正面为彼,反面为此,彼与此因道枢扭结而相通,自彼可达此,自此又可达彼,环绕不息,故而彼一无穷,此亦一无穷,而从“此”的视角出发所产生的是与非也自然能够相通而一无穷。然而是非来源于彼此之辩,故不能以言说道理来超越是非,言一旦出口,就又成是非之分别,因此圣人不言,照之于天。圣人怀而不辩是非,一旦是非在辩中彰显,真知就被遮蔽。而若彼此皆各明其所明,以自己之可为可,以自身所然为然,那么万物皆圆满有成。能认识万物各从自身出发的可与不可,才能和彼此之是非,这就是圣人所图的真知,得此然后达到忘义的境界,以自身所不是为是,这就是用真知之理和通是非,任其相化至无穷。
在前文提到的言说的问题上看真知,真知是根源性的彼,是绝对待者,因此它本身便无法言说。因为一旦言说,言说指向的对象与言说表达出的对象就成为有分别的二者;而这不一的二者等同起来,又生出第三样,以此类推,无穷无尽,却皆与绝对的真知不同。因此圣人怀而不辩,各止于彼我之分。彼与我不能相知,因此知止于不知,是至人所为。庄子有言,“以有涯之生随无涯之知,殆矣”,即是说人恒有不知,人不忘不知之知,行事方能得当。
至德者得真知,但其身有形,仍在相对待的彼是之间,以有形之身持真知的境界,其对应的是形有不得已而心不为所动。世间种种不测的偶然不会因至人是至人就不加于其身,就好像王骀成为至人仍不免受刑而兀足,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命。《人间事》中借孔子之口,说人间两大无所逃之戒,一曰命,二曰义。至人不得不因天理之固然而行事,又正因他们得真知,因此能够因天理之固然,然后不得已而表现出好恶,不得已而用兵、务世事,这些表现出的是非之彰,就是彼与此之不一,与人为徒,属人道。当幸而能不与人接而独处时,至者秉守无用以为养生尽年之用;而当因不得已而与人接,则至者能做的也只是缘中道、行应行之事以尽年罢了。然而至人之形可变,至人之心不可变。虽每至于纠结难为的不测境遇,至人如庖丁解牛而遇族,怵然为戒,但最终无论什么事情发生,至人都将所有结果等同起来。视丧其足,也不过如同一块土掉落;最极端的情况是死生之变,而至人却能视死生为一条,因其认识到生自身圆满,善其生与善其死者不过皆为大块独一者,故至者在生言生,不求所终。如此,至人可做到哀乐不能入,故虽不能免形体之罚,却能解遁天之刑。遁天之刑仅仅施于常人之心,而至人之心能不为动。至人因不得已而在外表现出的种种不一,在内心等同为一,这是以人道知天道,也体现了天人不相胜之理。至人能做到心不为所动,是因他们能守根源的彼,不以通物为所求而自然得通达之道,每遇滑涽,不能定夺,便置之不问,以众人所为为尊。至人从内心上无亲无偏,不以好恶伤身,因循自然,不以生为益,只是平常地身处自身圆满的生中,专注凝一,故能尽年。又因至人不随物迁,故能命物之化,这是至人对客观世界的影响。至人仅仅只是为己而不为爱人,自正其身,之后自然能正众身,利泽施乎万世,而这一结果并非至人所汲汲行之。然而彼是之分不亡,是非之争不息,所以有无圣人之才者,有无圣人之道者,有坐忘然后止于闻道者,总之有不能成为圣人者,这是圣人对世界的影响有限的地方。另一方面,圣人因循天理,“亡国而不失人心”,喜怒通四时而与物有宜,不以人助天而因天理务事。圣人以其得真知而影响世界,但其影响仍然是天道,是自然而成。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庄子哲学中完整的真知体系。至德者以有形之体承载无形的真知。无形者的本质在相互转化的彼与此以及根源性的彼这个三元的框架中得到诠释,其又以至德者为载体,衍生出对世间“用”的问题最得当的方法,与是非问题上能够超越是非之外的回答;有形者身处有形的世界,其形体与行为受客观性的制约与改变,但其无形的、得到真知的心能不为世间一切变化所动,故而能因其心、以其形,从而对世界有所影响。
谨以此文,向课程教师杨立华先生致谢。还记得您说,当您发觉自己走路带风了,就知道自己生活得太急、太快了。只有慢下来,才能从容地思考。这对于现在阶段的我们而言,是一件何其困难的事情啊!但仍然很感谢您的课程,让我有时间接近庄子的思想境界,也在我心中种下了一粒种子,每当我从生活的泥潭中短暂地接触到闲暇的空气,它就会悄悄地抽枝生长。我相信,这粒哲思的种子,最终一定能在泥潭之中,开出一树繁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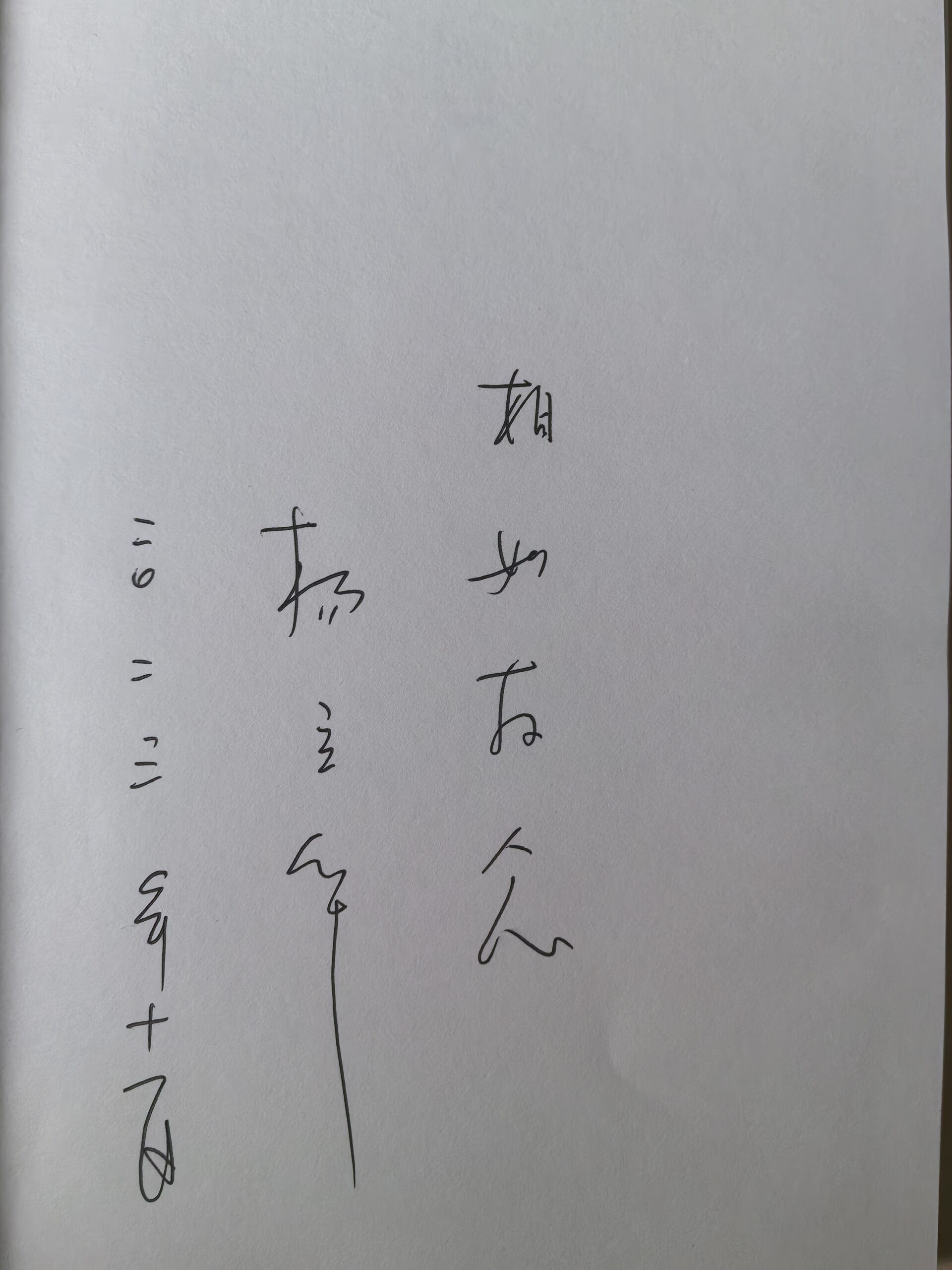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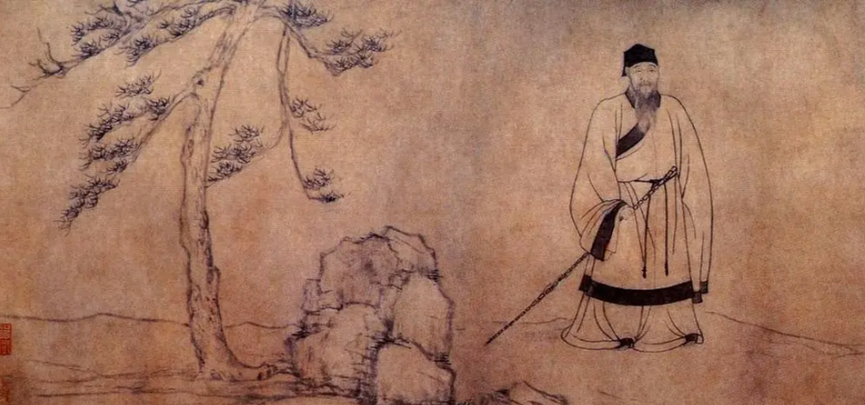
0 条评论